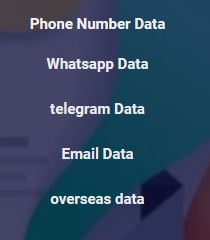我们可以争论古典主权理论是否是个好主意,但我们肯定有比评价几个世纪前去世的人提出的所谓解决方案有多好更好的事情要做。我感兴趣的是利用这种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主权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许多政治和法律参与者——总统和将军、士兵和记者、臣民和公民——并没有仅仅批评这一理论,尽管他们确实批评了。。这些斗争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它们有着(令人痛苦的)抽象的名字。宪政主义代表着我们可以限制主权权威的观点。联邦主义代表着我们可以分割主权权威的观点。法治代表着我们可以追究主权责任的观点。最后一种是不太成功的:主权豁免在侵权法中依然活跃且(极其)良好,其近亲外交豁免也同样盛行,即使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削弱了它的作用并具有追溯效力。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我试图将这些抽象概念带入现实。我重现了人们为主权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事件。因此,我想象了查理一世的审判和处决,以及弑君者的审判和处决。我谈到了正在展开的美国革命,当时英国坚持其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而主权明确地支持了这一权利(诺斯勋爵在捍卫一项经济上微不足道的税收时毫不妥协:“必须维持茶叶税,作为议会至高无上的标志,以及有效 智利 WhatsApp 号码数据 宣布他们有权统治殖民地”),主权的幽灵激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我深情地讲述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在殴打他的政治对手后傲慢地拒绝接受扰乱治安罪的逮捕——以及全国各地报纸对他傲慢的讽刺。“这让他自己变得可笑,”有人哼了一声。 “君主制的跳跃杰克,”另一个人大笑道。“从什么时候起,总督变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了?我们生活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政府之下?哪个?”我还举了一些国际法的例子:外交豁免权之争、加入国际联盟意味着放弃美国主权的担忧、英国退出欧盟以恢复主权的狂热运动。
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一些人对主权理论喋喋不休。他们吟诵道,每个政治共同体都必须有一个不可分割、不受限制、不负责任的权力中心。他们对批评者未能掌握这一基本真理感到震惊。但主权的拥护者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们以为自己在谈论世界上实际的可能性,但他们只是在诉诸概念的结构。问题恰恰在于主权概念是否有助于引导人们面对他们的问题和可能性,是否引导他们走向有吸引力的结果。而他们的批评者一再辩称,答案是否定的。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